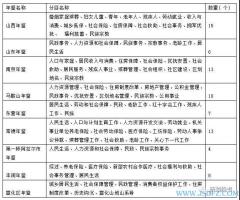地方志的学科属性及历史演变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关于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多少年来,人们往往着眼于方志的局部探讨——即方志历史化、方志地理学等,而忽视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方志本身的价值追求。宋朝以后把方志提到“一方全史”的高度,极力追求方志内容的系统化、完备化。直到民国时期,方志工作者才不断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审视、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今,知识文化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必然,方志与各学科密切联系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风土人情的自身特色。
地方志的起源之辩——“职方”与“外史”
自古以来,每当提到方志起源时,人们渴望能从古籍典章中找到依据或答案,或说源于《禹贡》,大部分学者认为源于《周礼》。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方志应源于周官职方,还有一些人认为方志出于周官外史。宋人司马光提出: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之地志,载方舆、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这就说明方志应为地理。然而,很多学者不以为然,认为方志由来已久,发源于《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这些观点莫衷一是,各抒己见。源于“职方”成为方志属于地理的依据,源于“外史”成为方志属于历史的证明,从而形成方志“史”、“地”之争的焦点。
方志无论是源于“职方”还是源于“外史”,都应完整、准确地理解《周礼》的原意。《周礼》不但详细记载了周朝的官制,同时对政治制度也做了大量的设想和勾画。虽然有些内容交叉重叠,头绪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就官制而言,则体现了一种认识各种不同政治区域有关情况的政治追求。其中既有方志职方所掌之说,也有方志源于外史所掌之论,仔细探究原委,周朝文化礼教虽然比较发达,然而,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局限,各种分工无法达到特别细致规范的程度,当然对于各地环境和社会情况的认知也不是一官所掌。
《隋书•经籍志》记载:“借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是故疆里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周则夏官司险,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土地;秋官职方,掌天下之图,盖总以为史官之职。”这就说明《周官》外史掌天下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聚史职,穷则侧陋之士,言行必达,一切皆有史传。
无论是解说地理类,还是杂传人物类,都涉及一定的方志内容,且与后世方志相符合。所以,记地、述人、职方、外史均与方志相关,不能简单界定职方和外史。周朝的司险、诵训、保章等也掌知地方情况,包括司会、形方、训方之类都对方志有所涉及。如果以一官之守或一面之情来阐释方志的起源与性质是片面的。司马光提出,修志是“为书以述地理”。而这一地理则是: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与先人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无不备载。《舆地广记》中也提到,所有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庶几可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可见,当时的外史与职方、史学与地理并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
元明以后关于方志源于《周礼》的说法在不同典籍中时有出现。但是,已经不局限于史地的简单划分,而是追求志书的多源性和全面性。《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言记事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吉凶祸福,无不当载。人们普遍认为,国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备,职方所司,外史所掌。清人王士祯抛开职方与外史之争,认为,志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己,《禹贡》所记山川田赋、《周礼》所载地图方志、《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皆方志所本”。这就完全取消了职方与外史的界限,同时也说明方志并没有源于地理和源于史书之别。
地方志的一贯追求——“全面”与“及远”
全面认识各地的不同情况始终是地方志一种明确的追求。从西周到战国,再到两汉至隋唐,地方志在探索中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志书形式有图经、地记和郡书等。郡书以记人为主,地记、图经以述地为主,这就导致了该时期志书的“记人”与“述地”二者分离。郡书因为单记人物,有了亦人亦史的性质,所以被一些目录列入了“杂传”或“杂史”类。而地记和图经以地理沿革、山川利害、贡赋物产为主要内容,从而被用作“地理”或“地貌”的证据。特别是图经,因以地图为主,则完全被纳入地理书的范畴。
宋元时期,随着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方志属于历史的观点渐渐成为主流,但以图经、地记为范式,主张方志为地理书的亦不乏其人。然而,持方志是历史的学者却认为图经不具备方志性质,不过是标明地理位置而已。可以说,记人与述地是某一历史时期部分志书的特点。如:《临海风土记》、《阳羡风土记》以风土为主要内容;《南阳风俗传》、《陈留着旧记》则以人物作为记述对象;《交州异物志》记物产、《洛阳伽蓝记》记寺庙道观等。这些著作单记地方的某一方面,因而被视为地方志书。但是,其中有些著作因为只对某一方面进行描述,又兼有其它著作的某些性质,则往往被列入杂传类,而有些如《洛阳伽蓝记》,由于只记寺观而认为它不是志书。这种志书的不完备性、不规范性是其探索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不能以此为依据说明方志的史地之别。
伴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全面认识和记述地方情况的社会需求日益凸显,并不断成为人们追求的学术方向。《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武帝时,郡国地志固已存在,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刘向略言地域,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彼叙。此后载笔之士,不能及远,但记郡名而已。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这段论述反映了社会上对部分史志书简化地情记载的做法不满意,一些作者因其经历,记述地方的某个方面有其意义,但不能成为一家之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人、地两个方面看待志书的倾向。
《隋书》之前,有一些作品如:三国时期的《三巴记》,不仅记沿革、水道之类,对地方郡的情况也有记载。晋代的《华阳国志》,于山川地理、政治兴亡、人物民族、大姓地望,均著于书中。陈寿《益部奢旧传》纵论古今,并不限于人物。羊玄之《洛阳伽蓝记》自序称,著撰园林、歌舞、兴亡之事,以寓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而已。刘知几虽以记山川、风俗、物产为地理书见长,但早已突破了人地风情的范围。他提出了这些书的本质特征:即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这一特征本身也是方志的追求目标,其宗旨是全面、深刻、具体。所以,自两汉起,志书已打破记人与述地、地理与史书的界限。元朝的志书,图以知山川形势,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特别是所记人才消长、社会盛衰、古今文化事实之故,更是全面周到,真可谓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下可以通治道之无穷。
方志是记某一地域历史、地理、风土、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述,长期以来,人们注意到了两汉至隋唐方志记人述地的分途,并以其某一方面的特点作为判定方志性质的依据。但是,在各种方志分别发展的同时,自战国以来人们对全面认识地情的追求一直在演进。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些地情记载的缺陷和不足。从整个方志发展史看,这种全面及远的学术意识追求是占主流的,从而打破史与地的分野,不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方志。
地方志的涉猎范围——“一国”与“一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明确提出,古之地志,载方舆、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主要原因是将古代的《禹贡》及图经作为志书的范本。《大清一统志凡例》则认为,舆地之书起于《禹贡》,所载山川、疆域、土壤、贡赋,盖简而尽矣。后班固有《地理志》,范蔚宗有《郡国志》,方舆之记,无出此外。按照这种说法,志书无外乎“载方舆、山川、风俗、物产而已。”清代学者在评价《太平寰宇记》时指出,地理而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为该书的短处。如果以此编定志书,必然体现出较明显的地理性。
纪晓岚的《安阳府志序》与《四库总目》的说法明显不同。纪昀提到:“志方域者惟《禹贡》《周礼》为可信,然古文简略,弗详尽也。志地理者始《汉书》,今之志书实史之支流。”然而,一代之地志与一方之地志其体例又不相同。修地志者,以史为根基,而不能全用史。与史相出入,而不能离乎史。也就是说,当时的方志已不是单记方舆山川物产的地理书。志方与地理不同,一代之地志是指断代的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志,可称为一国之志。一方之地志是指记载某一地方的志书,如府州县志之类。
“一国之志”的全国性总志是最早的一种志书。《贞元十道录序》中提到,自夏书禹贡,周官职方,汉志地理,继有其书。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朝代都有反映全国政区情况的志书出现。如《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元明以后,各代均有《一统志》的编写。这其中又有志书的变体“地图”和“图经”的产生。由此出现方志、总志、图经三者并存、各有其用的局面。这些志书记述的重点均在于版图地理,目的在于“灼知天下扼塞形势、封域户口、兵民财赋之要”。
宋代学者已经认识到全国总志因为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所记不得不简,这是总志特点所决定的,而郡县志则相对灵活详略自如。由于总志简略且侧重于政区地理,因此当代很多历史地理学者认为,全国总志不是方志。全国性总志与地方志书是志书中两个不同的类别。只能说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有很深的渊源。但是,全国性总志的内容主要倾向于政区版图,有很大的地理化倾向,这与追求全面性的地方志书有所不同。可以说,全国性总志只是方志中的一个类别,如果以总志的地理特征为依据,把方志简单定为地理书,既不客观,也不稳妥。
随着方志的发展,全国性总志亦有一种求全化趋向,但因容量所限,始终无法与地方志书相比。一国之志始于《汉书•地理志》。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各郡国的情况,因而有些论者以此作为方志的源头之一,有的以此作为方志地理说的依据。其实一国之志只是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的一部分。在纪传体史书中,政事、人物等内容各有所归,地理志不过是用于记述一代区划及各政区简况,与方志内容截然不同。所以,“一国之志”与“一方之志”并非一回事,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方志的科学分野——“衡定”与“改造”
20世纪后,西方学科体系进入中国,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方志理念。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在新的背景下跌宕起伏。一种新的学科尺度衡定着传统的学术问题,同时,国学同仁竭尽全力挖掘传统学术资源来适应新的方志发展,从而出现“衡定”与“改造”并行的局面。新标准科学趋新,老方志振作内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地方志的进步与发展。正如著名学者黎锦熙说的那样,居今日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及部门所能涵盖。因此,民国时期的方志已经进入新的学科轨道。尤其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掀起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提倡“进化史”,反对“循环史”;提倡“群体史”,反对“个人史”的史界革命,对方志的分野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学者把方志作为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探讨,并将方志与地方史相提并论。认为历史记载、研究人类进化现象,而地方志,也必须为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服务。所以,作史须注重社会关系、民生需求,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应是记载此一地方生育长养之序程。这就把方志完全划入史学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改造方志。如傅振伦说,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书重心已经明确。
在史学界的努力下,方志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地理学界也战旗高举,奋力将方志学纳入自己的范畴。他们主张:观察地理事实的各方面称为区域地理,这是我国的固有名词,也就是方志学。然而,这种观点受到社会的强烈反击。大家普遍认为,方志重在人事,若以地理言之,不仅失方志本意,就方志涉及的范围也将过于狭窄。所以,志属地理必然限制方志内容,这让方志的追随者无法接受。
近代方志性质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要求用西方尺度“衡定”,有人主张立足本土“改造”。然而,强调扩大方志的内容范围,要求方志观照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与传统方志的学术追求暗中契合,另一方面也适应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其本身就是方志理论的一大进步,使贯穿整个方志史的完备化追求和兼容并蓄的趋势得到极大程度的实现。
方志的对象是各区域地方,而每一区域地方都有包括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难以穷尽的万事万物。要科学地记述这些事物,反映地方的各种情况,必须有包括地理、历史、社会等诸多学科在内广泛参与。致使交叉学科人才及带着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入修志或研究方志的行列。从而,在方志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相关科学的发展变革。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学科对象所具有特殊矛盾性。恩格斯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所以,方志自产生之日起,便有全面反映区域情况的学术追求。其实,学科之间并无严格的“楚河汉界”。在很长时间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各学科间交相辉映,取长补短,决不能因为方志与历史、地理、社会的联系而将其简单地归入其中之一,也不能因为方志有着独立的学术追求而割断它同历史、地理和社会的联系。地方志是一个以地方为对象、兼容借鉴多种学术手段、方法及成果的综合性记述体系。方志发展的规律是方志系统内部结构相互联系、作用的反映。认识方志系统内部结构及纷争,可以预见和充分发挥其功能,从而结合需要,改变结构,实现对其利用和改造,使方志事业伴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