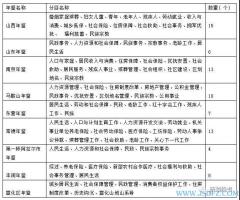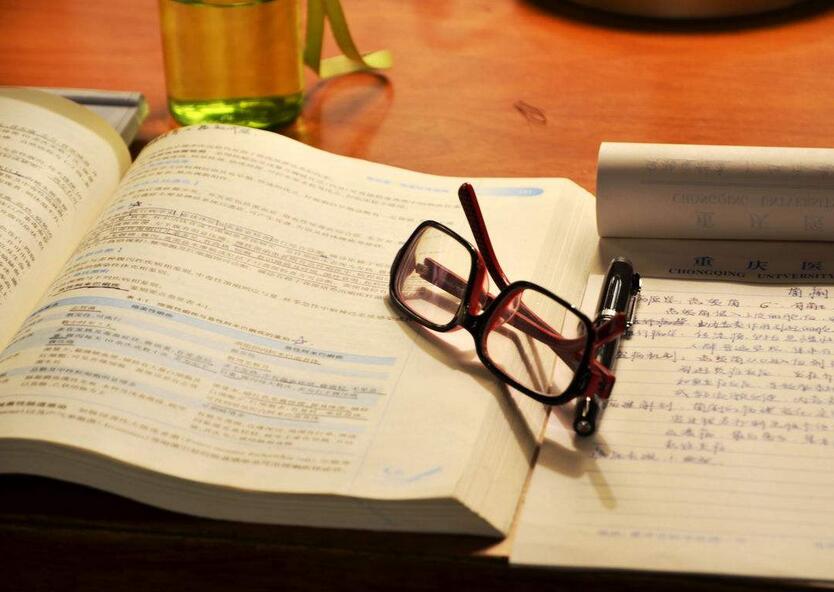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摘 要】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关键词】南宋,方志,理论,起源,性质,功能

南宋时,随着方志的转型与编纂的繁荣,方志理论逐渐成熟,但这些理论的表述非常零散,一直为人们所忽略。洪焕椿撰文《南宋方志学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进行了相关探讨。文章在总结范成大、梁克家、罗愿、陈耆卿、高似孙、周应合诸家方志理论与编纂实践的基础上,指出南宋时期我国方志学已涉及方志目的、作用、性质、内容、体例、编纂原则、编纂方法等。显然,洪文讨论的基础是存世志书,考察的范围与认识的深度仍然有限,很难动摇人们对清代章学诚对方志学研究的固有看法。南宋志书存世的虽然极少,序跋流传下来的却有很多。详阅这些序跋后,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学人对于方志的理论思考既丰富且深刻,已经囊括了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以及修纂人选、体裁与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等编纂学思想,完全可以与章氏学说媲美。编纂学思想已见于拙作《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本文将着重探讨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不确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方志起源
方志源自何处,是南宋学者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综合而言,大约有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周礼》说。《周礼》记载了“职方氏”、“土训”、“诵训”之职责,即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天下之图”、“地图”与早期图经的产生确有密切关系,故视《周礼》为方志源头亦不无道理。早在北宋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便提出此说,他在为宋敏求《河南志》所撰序文中,开篇即云:“《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明确将《周礼》作为方志源头,受到南宋不少士人的推崇,并体现在各自所撰方志序文中,如绍兴《严州图经》董弅序、淳熙《严州图经》刘文富序、淳熙《潮州图经》常祎序、庆元《成都志》袁说友序、嘉泰《太和县志》赵汝謩序、嘉定《仪真新志》吴机序、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等,皆持此观点,风靡一时。
其二,诸侯国史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均纂有国史,如鲁有《春秋》,晋有《乘》,楚有《梼杌》,在区域性这一形式上,与后世方志也有某种相似性,故被部分学者视为方志源头。宋宣和元年(1119),洪刍纂成《豫章职方乘》三卷,以“乘”为名,表明洪氏是认同方志与乘的渊源关系。绍定元年(1228),仙游叶棠由太府寺丞出知台州,请郡人林表民续《赤城三志》四卷,临海王象祖为之序。在序文中,王氏云:“今郡之图牒,古诸侯之国史也,《春秋》非鲁之史欤?”明确提出方志即古诸侯国史的观点。此外,开庆《临汀志》胡太初序、景定《临川志》家坤翁序等均称郡志为“郡乘”,或亦持此说。
其三,《九丘》说。《九丘》,相传为上古时九州之志,地理应是其记载核心。是书早已失传,今《尚书》有《禹贡》一篇,分叙天下九州山川、土贡等,或可窥见一斑。就内容而言,早期地记颇类《九丘》,故亦被部分学者视为方志源头。隆兴元年(1163),清源苏升以左承议郎知永丰县,续纂邑志,并序云:“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也。”即持此说。嘉定元年(1208),永嘉陈岘以集英殿修撰知广州,委托教授齐琥纂《南海志》十三卷,陈氏自序云:“九州之志见于坟典之初,至周诵训、职方所掌,事益加详,其由来古矣。”九州之志即《九丘》,显然,陈氏也是主张《九丘》为方志源头,周诵训、职方所掌只是它的继承与发展。
宋人关于方志起源的认识,直至现代仍不时有人提及,如傅振伦认为地理书、舆图、诸侯别国之书是方志三大源头,其中包括《禹贡》、《九丘》、诸侯国史,吕志毅认为方志起源于《尚书·禹贡》、《周官·职方》、《山海经》,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二、方志性质
提及方志性质,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派之论争,颇为后人津津乐道。其实,早在南宋,方志性质便已有地理与史学之分歧。作为定型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自产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均被视为地理之书,记载内容一以地理为主。北宋祥符初,翰林学士李宗谔受命领衔修纂天下图经,成《州县图经》这一巨著,在序文中,李氏云:“毛举百代,派引九流,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图经编纂中引入史学方法,对于推动方志性质转变功不可没。其后,赵抃、朱长文等人编纂志书时均强调资治、鉴戒功能,史学意识已经比较突出。北宋末,洪刍纂《豫章职方乘》三卷,以晋国史“乘”为名,史学倾向更是明显。
宋室南渡后,地理论的固有认识在士人群体中仍颇为流行,其中以洪遵、陈丰元、黄鼎、吴机等人为代表。洪遵,绍兴中以左承议郎权通判婺州,纂《东阳志》十卷,其自序云:“天下郡国之众,与时更易,旷不知其几千百载,欲举其要,非书不可也,由是地里之学兴焉。”明确表示志属地理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陈丰元以右通直郎知永丰县,纂《恩江志》十卷。在自序中,陈氏开篇便指出:“唐贾耽嗜书,尤详地理……已而相德宗,参赞辅翊,多所发明,是地理一书诚为有补于治道也。”这里“地理一书”当然包括现在所编纂的《恩江志》,说明陈氏亦是地理论的坚定拥护者。黄鼎,乾道五年(1169)官缙云县主簿。是年,知明州张津修成《四明图经》十二卷,黄氏受托撰写了序文,其中有“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图经”云云,将郡邑图经与《山海经》、《舆地图》归为同一类著述,属地理派当无疑问。嘉定十四年(1121),吴机以淮南转运判官兼知真州,委托扬子县令丁宗魏等纂《仪真新志》二十二卷。在序文中,吴氏明确指出:“诸州地图,十年一造,盖不以边郡而独置也,顾可终废而不续哉。”视郡志同于诸州地图,其地理派的立场亦显而易见。
随着方志逐渐成熟以及学术界对方志认识的加深,部分编纂者与地理派在方志性质上的分歧日益明朗化,史学派开始形成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乾道中,庐陵周因教授德安府,以本府多年未修图志,遂纂《郧地丛纪》一书,周必大赞其“深得史氏之体”,表明周因编纂时的史学倾向非常突出。此后不久,外戚郑兴裔立场鲜明地提出了方志即史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淳熙十四年(1187),郑兴裔知庐州,勤于政事之余,于次年委托合肥县主簿唐锜等纂《合肥志》四卷,并为志书作序。在序文中,郑氏阐明了其修志缘由在于“非徒以侈纪载也,盖有激劝之意”,以史为鉴的意识非常突出。继而略叙名贤烈女等遗事,并云:“垂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志属“史册”已表露无遗。修完庐州郡志不久,郑氏调任维扬守,再请州学教授郑少魏、江都县尉姚一谦纂《广陵志》十二卷。在这部志书的序文中,郑氏开篇便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更是明确提出方志即史,开方志史学派之先河。就在郑氏修《合肥志》的次年,知南陵县嘉禾郭嶤纂《春榖志》三卷,并请理学名家黄裳撰写序文,其中有“(郭嶤)又以余力攻图治史”之语,表明黄氏亦倾向于史书论。
宁宗以后,史学派的队伍逐渐壮大,高似孙、王象祖、赵与沐、家坤翁等便是其中代表。在序《剡录》时,高似孙指出,是书完成后,“剡始有史”,显然视《剡录》为史书。同样,在景定《临川志》序文中,家坤翁也主张“图籍视史册”,“图籍”自然是指方志。相比之下,王象祖《赤城三志序》与赵与沐《临汀志跋》表述明确得多,前者认为“今郡之图牒,古诸侯之国史”,后者指出“州有图志,一邦之史”,明显继承了郑兴裔的观点。此外,曹叔远纂有绍熙《永嘉谱》、嘉定《江阳谱》,周应合纂有淳祐《江陵志》、景定《建康志》,均被公认为史志体志书,虽无相关表述,然视四者为史学派似无疑问。
正当“史书”论日趋流行时,持反对意见者亦偶尔有之,以常州武进人褚中最具代表性。褚中,宝祐初举博学宏词科,授迪功郎、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时知平江府常熟县鲍廉重修《琴川志》十五卷,褚中受托撰写了序文。是序开篇即云:“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备记也,圣人之于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明确否定了志为史书论,认为方志乃“述史而备记”,即保存历史资料,与现代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志为“资料性著述”颇为类似,亦属一大发明。
三、方志功能
现代方志学者大多认为方志具有三大功能,即存史、资治、教化。其实,早在北宋时,便已有修纂者关注方志的某些作用,如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所谓“书乱臣所以戒小人,书寇盗所以警出没”,又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有“用备咨阅”云云。南渡后,这种思考更趋成熟。首次系统阐述方志三大功能的是东平董弅,董氏于绍兴七年(1137)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委托知建德县熊遹等纂《严州图经》八卷。董氏在为这部图经所撰序文末尾指出: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企高风而励名节。
“遗事略具”,备“职方举闰年之制”,也就是保存本郡资料以便朝廷修天下总志,实即存史;“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可以给当政者提供治理参考,实即资治;“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企高风而励名节”,既能淳厚风俗,又可砥励名节,自然属于教化方面。
其后,开封郑兴裔亦持相同观点,郑氏先后于淳熙末与绍熙初知庐州、扬州,分别主修《合肥志》与《广陵志》,均自为序。在《广陵志序》中,郑氏指出,志书能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同时,“圣天子采风问俗,藉以当太史之陈,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前有所稽”与备“太史之陈”均言存史,“后有所鉴”与后守邦者之“据依”皆论资治。又《合肥志序》末略叙名贤、烈女遗事,继云:“垂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所强调的乃是志书教化功能。显然,二者在方志功能方面的认识已经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丝毫不亚于后人。当然,关注某一个或某两个方面功能的,则比较常见,如楼淳等强调存史,张栻、陈耆卿、吴子良等强调教化,李昴英、黄岩孙等强调存史与教化,说明方志功能在当时已经受到普遍重视。
综上所述,南宋学人对方志起源、性质、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取得了重要成就。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志书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南宋的方志理论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方志之学臻于成熟。(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