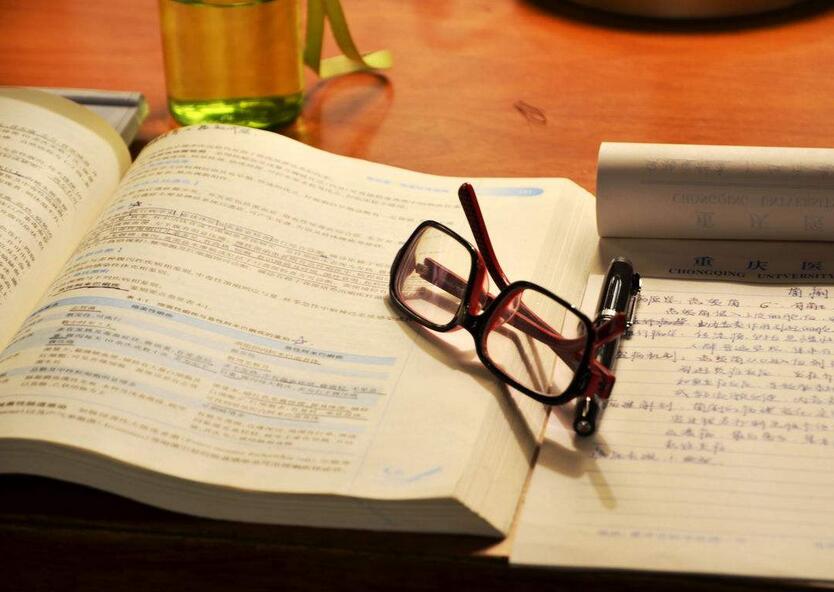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孙昊《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
在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深入剖析和检讨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总结一些有益的思考。此前原始社会向早期国家发展的酋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北族王朝的研究。因为无论是酋邦,还是部落联盟,其预设前提都是这个民族在没有受到周边社会影响,处于一个独立的、缓慢的自我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符合中国北方社会多民族交融、相互影响的发展实际。近些年来流行的所谓“内陆欧亚”视角,与传统中国民族史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这些学者并不承认北方社会的原始性或落后性,而认为北方的内陆欧亚社会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社会发展主体,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历史发展逻辑,不能用“原始社会史”的观念来理解。内陆欧亚视野下的北方民族相互联动的观念,无疑为孙昊的女真史研究拓宽了出口和可能性。
孙昊现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合作导师李锦绣研究员一直以内陆欧亚学作为本室学科建设的核心。受这种有利环境的影响,他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从事东北亚民族与内陆欧亚或内亚草原的关联性研究。他认为东北民族的发展与整个欧亚草原紧密相连。这一点并不仅体现在内亚文化的相似性,更多地体现在多族政治互动直接导致了东北民族的一些政治概念和政治关系的产生。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所著《危险的边疆》(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提到,东北民族往往是拾荒者,利用北方草原和南方农耕定居族群两败俱伤的机会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东北民族可以同时吸收南北两方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孙昊最近关注渤海国问题,也发现渤海王权的建构事实上凝聚了北方草原可汗正统性和唐代政治传统双重因素。因此,东北民族的发展可能较我们之前所了解的更为复杂。
理论不仅是一种视角和问题意识,还是挖掘史料新义涵的方法、工具。20世纪40年代政治人类学的“非洲经验”(参见[英]M.福蒂斯、E.E.埃文思·普里查德编《非洲的政治制度》,刘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促使后来的研究者意识到所谓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社群,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组织,这影响到此后研究问题意识的转向,并成为当代内陆欧亚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考出发点(如[美]Lindner, “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4, Issue4,1982,在国内近年罗新老师亦大力倡导)。这是政治人类学社会“常识”之更替促使历史现象认知改变,进而影响我们对现有常见史料理解的典型例证。因此,我们应充分跟踪,采用多学科的“常识”,投入到我们自身的“田野”工作——文献解读过程之中,变“常识”为“工具”,与文献所记述之语境进行深入对话,也能够得出新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通过自身的“田野”经验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在一个共同关注的理论层面进行对话、相互借鉴。
最后,孙昊总结其研究心得,指出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含多民族语言的文献)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地理、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在此基础之上,理论“常识”的转变对于阐释史料是最为重要的,但前提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常识”或理论,一定要像追溯史源一样地追究它们的知识源流,明确其终极问题趣旨,才能将其变为自己阐释与深翻史料的得力工具。